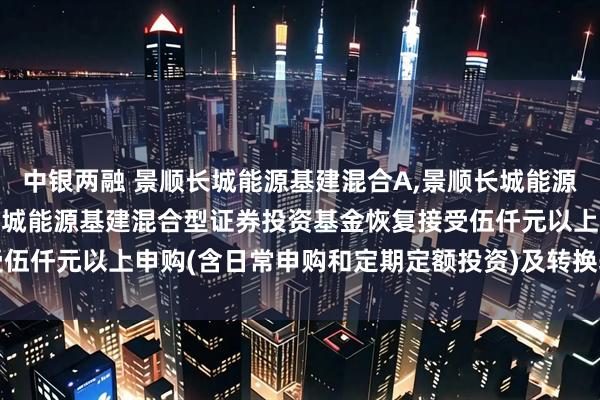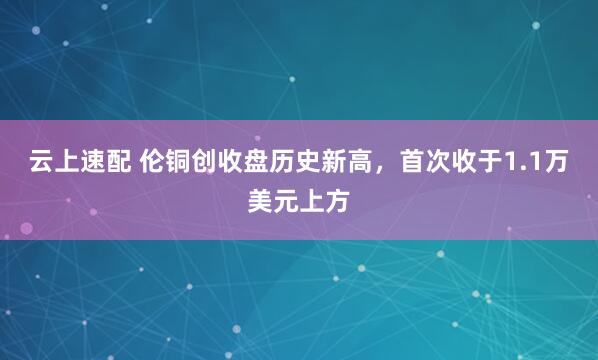三千年前,周文王在岐山渭水畔斩蛟龙以飨军民,釜中肉羹浇面,只啜其味而回汤入釜,让百姓人人得尝——这便是最早的“臊子面”。一口下去,酸辣鲜香智财资本,薄筋光韧,仿佛把周原的黄土、秦腔的高亢、关中的旷达全揉进面里,三千年不散。
要做一碗地道的陕西臊子面,先得把面团“三光”——盆光、手光、面光。以渭北冬小麦高筋粉,加盐碱冰水反复揉压,醒足时辰,再擀成“薄如宣纸、韧若龙须”的面条。臊子是灵魂:带皮五花肉切成骰子丁,小火煸出琥珀色油脂,下姜末、秦椒面、子牙陈醋、八角桂皮慢煨,肉粒油亮酥而不柴;另起锅,胡萝卜、木耳、黄花、豆腐干五色切丁,炒得清脆甘甜,是为“底菜”。汤要“煎稀汪”——滚沸高汤冲入醋与油泼辣子,汤面漂一层红亮辣油,酸香冲鼻,却清亮不浊。
展开剩余61%面条入水三滚即起,趁热浇汤,只捞一筷头,讲究“一口香”。碗小如茶盏,一人一次可连吸十余碗,碗碗滚烫、口口新鲜,酸辣在舌尖炸开,面条筋道弹牙,肉臊酥香、底菜爽脆智财资本,汤汁顺喉而下,额头冒汗,通体通透,正是关中人说的“撩咋咧”!
陕西人把日子也过成了臊子面:大年初一,晚辈端第一碗到门外泼汤祭天地,再敬祖先,称“福把子”,祈愿来年风调雨顺;红白喜事,主家支一口大铁锅,案板排开十几米,擀面声如秦腔过门,满村飘香,来客不论亲疏,蹲在门口吸一碗,便是最高礼仪。
如今,这碗面早已走出黄土高坡。在西安的感恩时代广场,“感恩有您”陕西一口香臊子面馆,玻璃橱窗后的老师傅仍坚持每日现擀、现炒、现炝,辣油红得晃眼,只为让舌尖记得家的方向。
如果说三秦大地是一部厚土史诗,臊子面便是其中最热气腾腾的章节——它把周礼的庄重、汉唐的豪迈、关中的粗犷、陕西人的热情,全都浓缩在一碗酸辣的红汤里。一口下肚,感受到八百里秦川的风扑面而来。
发布于:陕西省道正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沪深京指数
热点资讯